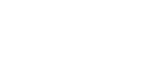文|公维章 山东泰山学院历史学院
第十六届吴越佛教研讨会暨飞来峰研究佛教造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

飞来峰造像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上,有五代至元代时期的佛教造像380余身,是浙江省最大的一处佛教造像群。位于龙泓洞洞口西侧的高僧取经组雕(编号为46、47、48龛),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与讨论,集中体现在对这组雕像的内容与雕刻年代的探讨。以赖天兵、劳伯敏、于硕的研究成果为代表。
赖天兵在《关于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几个问题的思考》中认为,第47龛前一位牵马者的题记"朱八戒"中"八戒"两字系原字磨损后改刻的说法,缺乏考古学依据,难以成立;第47龛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取经故事,此龛与第46龛联合组成为玄奘取经浮雕制作的年代为元代。劳伯敏在《再谈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兼答赖天兵先生》中对赖天兵的立论进行了质疑,认为该浮雕的内容并非是唐僧取经和白马驮经的两组,而是"白马驮经"、"朱士行取经"和"唐玄奘取经"三级;"朱八戒"三字题记乃"朱士行"之误,是指站在高处作指挥模样的第一人,该人原来应有头光,惜已剥蚀。"从人"几字是指两位牵马者。高僧取经浮雕是宋代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元代不可能产生。
于硕在《杭州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内容与时间再分析》中通过对朱八戒人物形象的出现时间、第47龛人物站位顺序以及"朱八戒"榜题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认为第47龛本应与46龛连接,讲述的同是唐僧取经故事,而第47龛中的三人二马为唐僧的随从,并推测高僧取经组雕的雕刻年代,很可能是在元代早期。笔者比较赞同赖天兵的观点,但赖先生并未对劳伯敏先生的质疑做出回应,对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展开深入讨论。本文就飞来峰第47龛的造像组合、玄奘取经图像的演变及宋元时期杭州地区的玄奘取经传说等问题,对浮雕的内容及雕凿年代与制作背景加以探讨。

▲飞来峰第46龛玄奘取经图 摄影|一叶
一、飞来峰第47龛的造像组合
关于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的内容,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有"唐僧取经"和"白马驮经"两组,二是认为有"白马驮经"、"朱士行取经"和"唐玄奘取经"三组。学者对第48龛反映的东汉明帝时期的摄摩腾与竺法兰"白马驮经"的内容没有疑义,对第46龛的唐玄奘浮雕也没有疑义。那么第47龛反映的内容到时是"朱士行取经"还是唐玄奘的取经随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整体对第46、47、48龛的内容加以分析。
对佛教造像内容的确定,造像题记是分析造像所属内容的首要依据,没有题记的情况下,则考虑依据佛经及其注疏文献与画史文献来展开分析。此高僧取经浮雕现存有8条题记,皆位于竖长方形框内,其中5条题记标明附近所刻人物身份,成为分析浮雕人物身份的重要依据。现存的这8条题记是原来所刻还是后来改刻?这是解决浮雕人物身份的关键所在。
第46、47龛的3条标明人物身份的题记位于人物行进方向的头部前方(人物的左前方),而第48龛中间人物的行进方面与第47龛相左,故题记刻的位置(人物的右前方)亦与46龛不一致。根据赖天兵文中的插图《第46-48龛取经浮雕平面图》所标注的题记位置,对8条题记的现状作以下交代。
A题记为"□岭"、B漫漶不识一字、C为"摄摩腾□□"、D为"竺法兰三藏"、E为"天竺来□□"、F为"从人"、G为"朱八戒"H为"唐三藏玄奘法师"。A、B、C、E题记改刻的可能性不大,争论较大的是G题记。劳伯敏认为G题记"朱八戒"中的"八戒"二字为"二行"的改刻,"八戒"二字"明显经后世重凿,但第一字‘朱’看来可能是原刻,而这正与朱士行的姓氏相符。"既然其它题记改刻的可能性不大,但改刻G题记的可能性也不会大。因为某种机缘,需要对此处题记中漫漶不识的字加以补刻,为什么A、B、C、E题记中漫漶的字不补,单要去补刻G题记的"八戒"二字?
据赖天兵观察,"龛中题记‘朱八戒’三字的刀法系一气呵成,没有两个年代合成的迹像,而且题记上下表面进深均匀一致,并没有应该出现的下部磨蚀。因此‘八戒’两字系原字磨损后改刻之说,缺乏考古学的依据,难以成立。"笔者同意赖先生的观察与分析,另外,改刻原来的题记并非易事。在敦煌壁画的榜题中有补写的情况,时过境迁,原来的壁画榜题漫漶清了,在重描壁画的同时,也一并将榜题补写,或者只补写榜题。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石刻题记的补刻并非如壁画榜题那样容易。众所周知,古代要将文字刻于石碑或岩石上,首先由书者将文字用朱砂作墨书写于石面上,称为"书丹"。【书丹,碑刻术语。即刻石(又包括碑、摩崖、造像、墓志等类型),必须经过三道工序:撰文、书丹、勒石。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勒石工序,需要有经验的石匠来完成,古代勒石的石匠绝大多数并不识字。据笔者考察,中国古代石刻文字补刻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碑刻文字有较多空余的空白处再镌刻其它内容的文字,或者是在造像碑中有较多空余的空白处镌刻与此造像无关的其它内容的文字;二是原来石刻文字漫漶不清了,由于某种重要原因需要用原碑的拓片或抄录文字或底稿将原碑文字重新镌刻。在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碑或窟摩崖造像中,现在还没有发现将原来漫漶不清的造像题记在原题记位置进行补刻的情况。因此,飞来峰第47龛"朱八戒"题记中仅将"八戒"二字改刻成"土行"的可能性不大。
对题记"朱八戒"所属人物,劳伯敏认为是第47龛前行的第一人,"从雕凿位置看,‘朱□□’位于题记的第一块,显然是指第一人。这个人物站在高13厘米的平台上,似作回头状,象是一位指挥者,在整组浮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惜上半身残损严重,原可能也是有头光的。"赖天兵则认为题记"朱八戒"所属人物应为第47龛中间的挂念珠、持杖棍的牵马者,"纵观飞来峰取经浮雕,人物形象都留有题记以表明其身份,题记处于龛中部一组人马的范围内,题记处于龛后部一组人马的范围内,题记的具体位置都在人物的前上方,这种规整划一的做法,没有给模棱两可的想法留下余地,‘朱八戒’无疑指龛中部,而不是前部的那位人物,‘从人’则是指后一位牵马者。"
笔者同意以上赖天兵的分析,因为整个46、47龛的人物行进方向一致,H题记的内容与有头光、身穿袈裟、双手合十的高僧像相吻合,因此G题记"朱八戒"即指第47龛中间挂念珠、持杖棍的牵马者;F题记"从人"指后一位牵马者。由于第47龛前行的第一人上半身残损严重,从下半身情形分析,其回头作指挥状的可能性不大,另从其残破的服饰来看,绝不同于整个取经浮雕中的三位高僧服饰,故其身份为高僧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上半身完好,其也不可能有高僧标示的头光。其前方肯定有表明其身份的题记,惜已毁失不存。
从第48龛残存图像及题记分析,反映的内容为东汉明帝时,郎中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以B题记后的人物为代表,此人面向摄摩腾作礼拜状,题记位置亦与两位高僧的题记位置不同,标明此人应面向摄摩腾)前往天竺,迎请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从天竺出发,白马驮经,行进至逼迫葱岭的场面。此事件标志着佛法传入中国之始,这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碑刻中随处可见,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如果第46龛玄奘独身一人表示"唐三藏取经"似于第48龛不相协调,因为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取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因此,从第47龛牵马前行的三身人物的装束来看,应该是第46龛玄奘的随从,三人的身份是行者,还不是受具足戒的僧人,绝不是学者所认为的是表现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于阗取经的内容,并且"朱士行取经这一题材在佛教艺术中似找不到先例,甚至尚找不到同例。"

因此,第46龛与第47龛的关系正如常青所言,"第47龛的三身雕像均不为中国传统僧人的装束,且都身佩兵器,明显具有随行护卫的身份,行进的方向也与第46龛的玄奘相呼应。所以,笔者认为第46龛与第47龛应为一组,可统一命名为‘唐僧取经图’"。通过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第48龛东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与竺法来携经、像从天竺东来,二是第46、47龛联合表现的唐玄奘及其随从从天竺取经东归。此二组图像组合在一起的原因,除以上笔者所论二者皆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外,或许与南宋后期或元初杭州地区盛行水陆有关。
水陆法会是佛教追荐亡魂的一种宗教仪式,举行法会时要祭奉众多的神祇。这些神祇通常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包括壁画、卷轴画、版画等。赵宋之时,水陆法会始为南、北。在宋元明清时期,南水陆法会主要盛行于四明(宁波)和杭州地区,其修斋仪轨为《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每年的中元节,各地大都举行盛大的水陆法会,每会必有水陆画,起码宋元时期的杭州地区,水陆法会必有包括摄摩腾、竺法兰、玄奘在内的祖师画像,或以其他禅师共为一帧,或三法师单独一帧。因此,宋元时期杭州地区的画工是极为熟知这一题材的,将三法师各配以取经随从,将这一题材雕刻于佛教氛围浑厚、寺院林立、佛像集中的飞来峰,以向世人昭示取经之不易。
之所以将第47龛的三身人物称为玄奘的随从,原因是既然该高僧取经组雕的雕凿年代为元代,从现存明代以前不同阶段玄奘取经图的人物组合来看,还未见有"朱八戒"这一人物的出场。于硕通检了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有关的文献材料,主要包括《西游记平话》、《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销释真空宝卷》与《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等,图像材料则主要为现场磁州窑瓷枕上的取经图后认为:
记载有朱八戒的取经故事资料较为有限,或为残本,或几经修改增补,依现存几种重要的文献与图像资料推测,西游记在元明清三朝应存有多套体系,它们之间也并不孤立,而是有着一个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朱八戒人物形象可能属于诸体系中的某一支,产生于元代末期,并由《西游记》杂剧的搬演而传播开来,但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中的人物形象是否为朱八戒却不能因此简单断定。依以上分析笔者怀疑,《西游记》杂剧于钱塘地区流传开来之后,可能有人将榜题改刻,但改刻的时间也不必限定于元代,因为在明初这个人物还被叫做"朱八戒"。
于硕经过详细考证,推测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的雕刻年代为元代早期,而通过对现存记载有朱八戒的取经资料的审慎考察,认为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于元代末期,据此而怀疑飞来峰第47龛的"朱八戒"题记为后人改刻。但据笔者研究,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于南宋后期或元代早期,见于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瑜伽教科仪文献《佛门受生宝卷》及相关文献。

二、"朱八戒"最早出现的年代
诚然,考察朱八戒这一人物形象出现的年代,关乎对飞来峰高僧取经浮雕雕刻年代的判定,与玄奘取经故事有重要关联的瑜伽教斋会的科仪文献基本还未进入玄奘西游故事研究者的视野,据这批文献的整理者侯冲认为:"本科仪与小说《西游记》在某些情节上比较接近,但亦有明显区别,对于《西游记》研究有重要价值。由于以往未被《西游记》研究者注意,相关资料亦未纳入《西游记》研究资料,故本科仪为《西游记》研究的新资料。"侯冲整理的这批文献皆为抄本,其抄写年代为晚清民国,但对这批文献的性质与成书年代,侯先生认为:
本科仪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均有抄本流传。是以《佛说受生经》为根据编集的瑜伽教道场仪,为荐亡法会科仪文本。本科仪是《佛说受生经》深入民间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证据。由于瑜伽教明初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瑜伽教道场仪往往严格秉承师传而鲜有新增加的内容,该科仪的部分内容并见于清乾隆年间抄本《开坛请圣》、《佛门迎经科》等瑜伽教道场仪,故推断其成书时间不晚于明初。
但根据这批文献中的避讳及所引故事,笔者判断其成书年代或部分内容的成书年代要早于明初。
根据文献的演变规律,清同治十四年、清咸丰三年及民国二十九年抄本中的"小僧手下徒弟,名号朱八戒、僧(孙)行者齐天大圣"为该类文献的最初内容。清光绪六年抄本"小僧有徒弟三人,一名孙行者,一名猪八戒,一名沙和尚"明显为三者同时出现的元末明初《西游记平话》与《西游记》杂剧之后,特别是百回本《西游记》流行之后所作的改写。清同治十四如何用清光绪六年抄本韵文中"孙行者"、"朱(猪)八戒"与"沙和尚"亦为元末明初之后所为。另外,以上所引《受生宝卷》等科仪类文献中的"正观殿上说唐僧,发愿西天去取经"与此句相关的"小僧手下徒弟,名号朱八戒、僧(孙)行者齐天大圣"为此类文献最初内容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唐玄奘印度取经的随从"孙行者"与"朱八戒"同时出现的年代为南宋或元初。
宋元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佛教伪经《佛说受生经》(或作《寿生经》),该经目前发现两种版本,第一种为黑水城出土的金代抄本,该经无唐玄奘于贞观十三年西天取经的内容;第二种为入藏本,该版本目前发现三种,一为明《嘉兴藏》本《诸经日诵集要》卷中所收《佛说受生经》,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刊本,存首部,封皮署"连相寿生经",卷首有扉画,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天顺七年(1463年)刊本,存尾部,说明此种版本在明代广为流行。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佛说受生经》:"正观十三年,有唐三藏法师往西天求教。"说明此经在北宋仁宗以后或南宋时期在宋地及金地流行。另外,现存较早的明确寿生寄库信仰实物资料是宋明道三年(1033年)《福建路建阳县普光院众结寿生会劝首弟子施仁永斋牒》,说明早在北宋时期《佛说受生经》就已撰成并流通,依照此经结成的寿生会随之出现,在此斋会上行用的斋仪文一并出现,并引导此等斋会的举行。
综合以上考察,载有玄奘取经故事的《受生宝卷》等科仪文献在宋代以后的受生寄库大斋会上频繁行用,其一经产生并成熟后,往往严格秉承师传而鲜有新增加的内容。因此,此类文献的绝大部分为原来的样貌,只有较少量的删改,因此,此类文献所记唐玄奘西天取经及其随从"孙行者"与"朱八戒"同时出现的年代为南宋或元初。

三、飞来峰玄奘取经浮雕的雕凿年代与制作背景
依据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说法,西游记流传之阶段,应分为唐宋著述或笔记中散见的取经故事阶段,生意人玄奘取经图像在画史资料有不少记载,也有少量的实物遗存,对此敦煌研究院的刘玉权有系列文章考察,因飞来峰玄奘取经浮雕的雕凿年代关涉不大,兹不赘述。

榆林窟3窟"唐僧取经图"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阶段,此类玄奘取经图像有不少遗存。最早的依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制作的玄奘取经图见于陕北宋金石窟。据石建刚考察,陕北延安地区宋金石窟中保存有14例《玄奘取经图》,这是目前所见这一图像最为集中、且时代最早的地区,通过图像对比发现,甘肃、山西、川渝等地的玄奘取经图像均与延安宋金时期研究中的玄奘取经图像关系密切,表现出一定的传承性。此14例《玄奘取经图》只有陕西子长县钟山石窟第12窟有明确的纪年,该窟石壁上部水月观音造像龛右上侧有题记"清信张氏修观音菩萨一会,永为供养。政和二后(1112年)九月二十日记。"钟山第10窟水月观音图像中的玄奘取经图约镌刻于1100年前后,早于第12窟的取经图像。樊庄第2窟前壁西侧壁面的水月观音图像中玄奘取经图约雕刻于1096年到1113年之间。富县石泓寺第7窟的玄奘取经图约雕刻于1141年到1154年之间。
川渝地区有3例与陕北宋金研究窟同时或稍晚的玄奘取经图,一例在四川泸县延福寺石窟,其时代在1114-1118年前后;第二例在重庆大足石窟的北山第168窟和妙高山石窟的罗汉洞,其时代分别为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

陕西渭南韩城大禹庙-----明代西游记壁画
稍晚于川渝地区的西夏瓜州及其附近地区的7幅玄奘取经图壁画均为西夏统治瓜州时期所绘制。分别分布于榆林窟第2窟西壁门北侧水月观音右下角、榆林窟第3窟主室门南普贤变正中南边缘、榆林窟第3窟主室东壁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下部、东千佛洞第2窟中心柱相对两侧壁,即甬道南北各有水月观音一壁,在观音座前画面中部各有一组玄奘取经图,另有2幢位于甘肃张掖文殊山古佛洞石窟前壁窟口上方,其时代距东千佛洞第2窟的图像年代接近。绘有《玄奘取经图》的榆林窟第2、3窟及东千佛洞第2窟的绘制年代当在1168年前后。因此,瓜州及其周边地区的7幅玄奘取经图均为西夏晚期所绘制,说明玄奘取经故事在西夏晚期的瓜州及其周边地区特别流行。
这一阶段的玄奘取经图就图像结构而言,均非单体构图,而附属于其它主体经变图像,但出场人物均主要有玄奘、猴行者和白马,有时白马不出现,有时出现其他内容,但皆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玄奘的传奇经历有关。陕北宋金石窟中,作为玄奘取经图的主体图像,皆为水月观音;川渝地区的玄奘取经图的主体图像稍微有所变化,四川泸县延福寺研究的玄奘取经图的主体图像为水月观音,大足石刻的主体图像分别变为十六罗汉和五百罗汉;瓜州与张掖的玄奘取经图的主体图像多为水月观音,也有附属于普贤变、十一面千手观音变,表明主体图像并不固定,同时作为附图的《玄奘取经图》构图亦不固定。但从定阶段的玄奘取经图的图像构成要素分析,都受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影响。据学者研究,南宋于杭州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创作时间应该在北宋仁宗年间至南宋高宗年间,而且极有可能是北宋中后期的作品。陕西子长县钟山石窟第12窟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水月观音造像已有《玄奘取经图》,此图深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影响,因此《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至迟在北宋后期即已成书,且成书后在北宋的长安、洛阳(此二地为玄奘生前重要的活动地区)极为流行,并已出现了依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创作的最早的《玄奘取经图》。
从目前发现的玄奘取经图像较为集中的陕北石窟、川渝石窟及瓜州与张掖石窟,皆与玄奘生前莅临该地有关,这些地区应该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玄奘崇拜极为流行的地区,出现最早的玄奘取经图与玄奘崇拜有重要关联。
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阶段,相关玄奘取经图像关注不多,这一阶段,玄奘师徒四人及白龙马已经配齐,学者们关注的两块带有所说是元代的玄奘取经图像的瓷枕上的图像,以及据说出土于河南某地金代墓葬中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应为此一阶段的产物。
因此,杭州飞来峰的玄奘取经图在玄奘取经图像的发展史上,是一幅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作品,因为其取经队伍组合的四人皆有题记,并且为最早的独立出现的玄奘取经图,大约与山西运城稷山县青龙寺的唐玄奘取经图稍早或同时。青龙寺的玄奘取经图位于该寺的大雄宝殿门上方的拱眼处第三幅,画有三人一马向东前行,与画面反映的"白马驮经"、"取经东归"相对应,是一幅表现玄奘取经的独立画幅的图像。虽没有题记,但根据图中的白马驮经,经卷放射出五彩光芒,牵白马的猴行者的形象判断,其图像构成与杭州飞来峰的玄奘取经图有较大差别。
青龙寺的玄奘取经图继承了陕北宋金石窟的"一僧一从一马"的组合方式,又加入了随从僧一人,而飞来峰的玄奘取经图的组合方式是"一僧三从二马",显然各自根据的文本有较大的差异。青龙寺的玄奘取经图的创作依据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参照了前期流传的玄奘取经图,与陕北宋金石窟图像更为接近,而飞来峰的玄奘取经图的创作依据为南宋后期或元初的《受生宝卷》等科仪类文献或与此相关的玄奘取经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南宋至元代中期之前,南方与北方各自流传着不同系统的玄奘取经故事。元代统一中国之后,两套系统的玄奘取经故事才开始融合,产生了大体一致的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
因此,杭州飞来峰的玄奘取经图是产生于南宋或元初的《受生宝卷》等科仪文献中的玄奘取经故事,此一阶段是玄奘取经故事中的重要一环,应该引起玄奘西游故事及玄奘取经图像研究者的注意。
杭州飞来峰玄奘取经图的雕凿背景应与宋元吴越地区特别是杭州玄奘取经故事的盛传有重要关系。玄奘西行求法前,曾游学过大半个中国,到达过浙江的绍兴。据《大唐西域记》卷后《记赞》载:"玄奘法师者……负笈从学,游方请业,周流燕赵之地,历览鲁卫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吴会。达学髦彦,遍效请益之勤;冠世英贤,屡申求法之志。"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峡,经途所及,荆扬等洲,访逮道邻,莫知归诣,便北达深所,委参勇铠。……仆射宋公萧瑀,敬其脱颖,奏住庄严,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吴蜀,爰逮赵魏,末及周秦。预有讲筵,率皆登践。"
根据相关文献,玄奘圆寂之后,玄奘西行求法前与西行求法的中国西部地区,玄奘特别受到崇奉,相关玄奘的传说及美术作品在这些地区较多出现,应与此相关。玄奘既然到过浙江,也游学拜访过杭州的高僧,杭州的玄奘崇拜应表现极为突出。
据日本学者竺沙雅章考察:两宋之交,原定州仙林寺智卿(?—1163)到临安(今杭州),见"慈恩将坠,不复流布",志愿复兴慈恩宗派,刊刻了"慈恩及宗乘疏钞"。绍兴十三年,右武大夫蔡通等出资,在盐桥北修建寺院。绍兴三十年建成,宋高宗赐名"仙林慈恩普济教寺",由智卿主持。智卿在此弘传唯识宗,从此直到南宋后期,此寺院一直致力于弘传唯识宗。南宋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十五"城内外寺院"条:"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在盐桥东。寺有万善大乘戒坛,僧尼受戒法之地。"杭州的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应为杭州著名的寺院,且作为杭州僧尼受戒之地,其在杭州寺院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其弘法特色使之成为玄奘崇拜的一个重要中心。
宋代民间即流行受生斋会,宋元时期杭州更是极为流行,南宋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十九"社会"条:"宝俶塔寺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会。"元代南宋遗民方回《桐江续集》卷21《记三月十日西湖之游吕留卿主人孟君复方万里为客》:"丙申上已七日后,一主二宾夫岂偶。遣车却骑钱塘门,主人满船冨殽酒。别唤轻船载仆从,大船品字着三友。旁观指点知为谁,对峙玊人间白叟。岂无识者讶此老,不愧妙年两贤守。孟侯吕侯将相家,早绾金章纡紫绶。方干云孙耸吟肩,左右鼎鼐中瓦缶。虽然兰臭尚同心,剧谈锋起各虚受。是日杭人诧佛事,焚寄冥财听僧诱。公子王孙倾城出,姆携艳女夫挈妇。放生亭远骛长堤,保俶塔高陟危阜。居然红裙湿芳草,亦有瑜珥落宿莽。暖热已极天色变,大风滔天怒涛吼。篙师缭绕孤山背,倘佯里湖保无咎。百舠千舫第二桥,四圣观前依古栁。"
上文讨论的《受生宝卷》等科仪文献为明代以来瑜伽教僧所用科仪。瑜伽教,或称瑜伽教、瑜伽门,源于唐代的佛教密宗,讫于宋元明时期,是流传于民间社会的一支民间宗教,该教派仪式活动颇具特色。自南宋以来,该派法师以云游的方式活跃于乡土社会,为民众提供驱邪、度亡等宗教服务,成为民间社会的"仪式专家"。因此可以推断,宋元时期杭州地区也成为瑜伽活动的重要区域,受生寄库斋会盛行,斋会所用的斋仪文献《受生宝卷》等科仪文献广为流传,成为宋元时期玄奘取经故事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
综合以上考察,杭州飞来峰第46、47龛高僧取经图像共同组成《玄奘取经图》,从造像组合、造像风格、造像题记及造像的独立性诸因素分析,应为创作于南宋晚期或元代早期的一件作品,此图的创作与杭州地区浓厚的玄奘信仰及取经传说有重要关联。玄奘西行求法前曾游学浙江;北宋后期形成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道场——香山来源于蒋之奇《大悲菩萨传》,此《传》在1100年蒋之奇担任杭州知府时刻碑于西湖天竺寺,现在最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刻本为南宋杭州"中瓦子张家印"本;宋元时期杭州有弘慈恩宗的寺院——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宋元时期杭州西湖宝俶塔寺每年春季举行受生寄库大斋会,斋会上要念诵《佛说受生经》、《受生宝卷》,此为瑜伽教重要道场仪,瑜伽教中的玄奘取经故事对杭州飞来峰《玄奘取经图》有重要影响。
撰文|公维章
编辑|慧容
责编|妙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