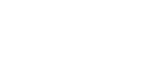五代禅师贯休《十六罗汉图》在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中乾隆时期供养于杭州圣因寺的版本内容完整,形象生动,甚至被认为是贯休真迹,这样的作品在被进献时却由乾隆归还原寺典藏。但不藏于内府并不代表不被重视,乾隆皇帝将其进行考订、修理、命人临摹等,之后这套《十六罗汉图》的刻本、临本等不同媒材的版本得以广泛流传。这样的现象值得关注。

二、乾隆皇帝对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的鉴藏行为
乾隆皇帝与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的鉴藏活动,主要集中于其第二次南巡前后。在六下江南的旅途中,乾隆皇帝携带大量的书画供路上赏玩,子明本《富春山居图》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该卷上有乾隆五十余处题跋,是他对这件作品珍重程度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他南巡生活的绝佳记录。南巡期间或南巡前夕,臣子向皇帝进贡作品的例子并不罕见,这些作品一旦被选入内府,或随皇帝一同南巡,如乾隆二十六年由尹继善进献的《福禄攸同》图轴,“二十七年带往南巡,行宫看地方挂。”或直接送交内府保管,如乾隆二十二年马负书进献的《闽省物产》图册,“差人送京交三和。”像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这样不被收归内府,又在南巡途中获得反复关注的作品并不常见。以下将按照南巡前、南巡时、南巡后三个时段分别叙述乾隆皇帝与圣因寺藏本的互动。
(一)第二次南巡前
1757年第二次南巡途中并非乾隆帝第一次观摩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裘曰修的一段跋文中称:
唐画世不多觏,乾隆甲子(1744),修蒙恩入直卢,始获见数种。己巳(1749)有奉使南镇之命,道出武林西湖圣因寺,又得《贯休罗汉》十六轴。辛未(1751),寺僧大恒赞祝圣母皇太后万寿,来京师,遂持以献。皇上谓佛刹旧物,应归名山,仍以还之。修既喜此段是绘事家佳话,亦可添佛门一重公案。然又窃念此十六罗汉者,不得入秘殿珠林中传不朽,他时或为妄庸子所夺,因笑语大恒,当为作记述此事,以垂示后人。

可见,乾隆至迟在1751年就已经见到过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当时圣因寺住持大恒欲将此画献于皇太后祝寿,被乾隆以“佛刹旧物,应归名山”为由退还。这样的现象似乎是不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乾隆皇帝的了解,他是一个狂热的鉴藏爱好者,遇到珍贵的作品,定会想尽办法将其收入内府。但乾隆成就“佳话”的意图却较常见,如为金山寺补足玉版:“藏金山寺中,曾遭回禄,缺数版,为补足制匣,仍去镇山门,以成佳话”等。或为塑造自己圣主明君的帝王形象,或为文人式藏家的鉴藏理想,乾隆皇帝在鉴藏活动中欲成佳话的心态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裘曰修所表现出的担忧态度也值得关注,他一方面喜于罗汉图继续供奉在圣因寺,于艺术于宗教都是一段佳话;一方面忧于罗汉图没有好的保存环境,日后为妄庸子所夺而不得传不朽。这种矛盾的心态是可叹可敬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当时,除了朝廷内府之外、包括寺庙在内的艺术品收藏、交易环境都难以令人信任,说骗作伪之事常有,人们已经重视到了这一点,同时,清人对文物的保护、著录意识也近乎是空前的。而事实上他一语成谶,昔日的圣因寺藏本今日已不知所踪了。

(二)第二次南巡时
乾隆皇帝于1757年第二次南巡在圣因寺见得十六罗汉像,有《贯休十六罗汉像赞》云:
唐贯休十六应真像,自广明至今垂千年,流传浙中,供藏于钱塘圣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驻西湖行宫,诣寺瞻礼,因一展观,信奇笔也!第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音,其名次前后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爰以今定《同文韵统》合音,位次于原署之下,各题以赞,重为书签,仍归寺中传世之宝。夫四大本无,画于何有?仍斤斤于名相文字之别,得毋为诸善者诃耶?御题。
乾隆皇帝将认为错误的音译和位次加以订正,重新为其署名、题赞,并将这一事件记录下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有乾隆皇帝命丁观鹏临摹此画的记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如意馆)初八日,接的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三月三十日,侍郎裘曰修带来贯休罗汉十六轴,首领桂元传旨交如意馆,着丁观鹏将面相、衣纹俱照依勾出,其余手足等处,若合法者,不可重改;若不合法者,遵照从前指示之处改画。至山子、石头,着王炳画。将现在承办之画俱行暂停,先将此项办理。钦此。于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催总德魁将画得罗汉十六轴进讫。

记录中提到“不合法”之处需改画,可见丁观鹏的临作及之后依此而来的石刻作品不完全与传为贯休的原本完全相同。此处之“法”由乾隆“从前指示”,可见丁观鹏此次奉旨摹画并非宫廷画师首次奉旨临摹罗汉类题材作品,在此之前,乾隆皇帝便至少已经对罗汉画在图像上做了规范。此外,乾隆皇帝命丁观鹏将其他绘画任务一律暂停、优先绘制此话,足见重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记载了在接到临摹此画的任务之前,丁观鹏奉旨拟卢楞迦笔意绘绢本、纸本《释迦及十六尊者像》,此套作品由丁观鹏先“起稿呈览”后又完成,起稿的标准极有可能成为后来仿贯休罗汉之“法”。
(三)第二次南巡后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南巡回去后,命丁观鹏进行摹画,又考订、重装,退还圣因寺。乾隆二十九年,圣因寺住持募资将其摹勒刻石,供于圣因寺中,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圣因寺十六罗汉像。自此之后,这个经乾隆题赞、译名、排位后的石刻版本成为了具有范本性质的底本,成为清代中后期罗汉画创作和著录的标准。石刻本的拓片被带去其他地区,做成新的刻本,如:李宜民于乾隆五十八年以圣因寺刻本为底本,在粤四隐山华盖庵摹刻一套,现藏于桂林市文管会。乾隆还依此命人制成了十六罗汉屏风、罗汉赞墨等,至此,《十六罗汉图》不同尺寸、媒材的版本广泛传播开来。类似的作品还有董邦达等为南巡所绘制的杭州与苏州风景图像,作为装饰和传播在宫中不断被复制成各式各样的版本。

更晚之后的乾隆六十一年,皇帝重阅《秘殿珠林续编》著录的明《吴彬画十六罗汉图》,命董诰代为题跋,提到此本与西湖圣因寺藏本互有同异,推断是贯休“所画原非一本”之故,称“佛法即空、即色,一切法化报身皆非我相,是一、是二原不必作分别想。”表达出不必纠结于其版本与是非之中的态度。之后又说原画自标的位号、次序有误,以西蕃梵夹合音订正、重排,即正是按照其纠正过的圣因寺本的次序和位号。
可见,经由乾隆皇帝此番“互动”后的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一方面其内容和样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权威版本,石刻的版本更有助于供奉瞻仰,也有利于传播和示范。而经皇帝订正的位号、次序,则成为此后罗汉像绘制、鉴藏、著录的标准。
(摘录自《吴越佛教》第14卷)

这是一组日本江户时代十六罗汉画册;明显临摹了五代贯休的罗汉特征。画像中的人物,浓眉深目,大鼻隆突,胡须络腮,肤色黝黑,神情脱俗,带有浓厚的异域特征。他们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态。通过十六罗汉的各种日常坐姿与朴实无华的动态,致力于刻画罗汉们超凡入圣的神态。性格各异,呼之欲出,格调极为高古,而更接近罗汉“杀贼、应供、无生”的本义。是临摹贯休罗汉图作品中的的精品佳作。